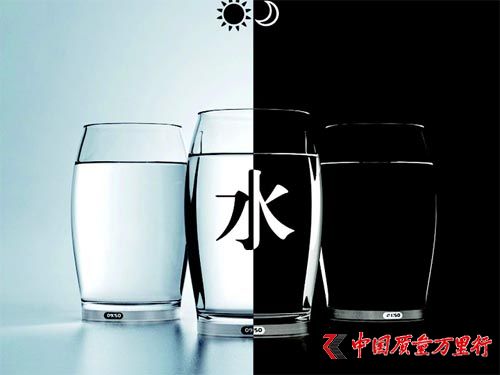今年4月底5月初,洛克線和鰲太線接連出現驢友失聯死亡事件,引發外界各方面的熱議。
隨著驢友出游涉險失蹤或者死亡的事情頻繁發生,所以搜救所產生的公共資源費用也越來越多。當個人涉險冒險旅游引發出來的一系列的公共事件,一場爭辯不可避免:這個人涉險出游所帶來的危險,繼而產生的公共營救該由誰來買單?是全社會還是出游者個人呢?

驢友經常失聯引發搜救根據國家登山協會所給出的“2016年登山戶外運動事故分析報告”可以看出,2016全年共發生311起登山戶外運動事故。雖然這些事故基本得到了公安、消防、民間救援隊等機構的及時救援,但仍然有多起事故傷亡案例。2016年全年事故中活動參與總人數1813人,發生事故總人數1268人,受傷事故114起,受傷人數146人,死亡事故54起,死亡人數64人,失蹤事故3起,失蹤人數3人,無人員傷亡事故140起。
對此,一些資深的驢友或者業內專家指出,許多驢友之所以遭遇危險,主要因為是在缺乏專業安全保障和未在相關部門辦理備案登記的情況下進行違規徒步活動。而為了營救這些被困驢友,公安、消防等部門要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營救人員也會多少出現一些人身危險。
驢友徒步時出意外,很多時候都是因為自身的問題而產生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展開的公共救援工作是算誰的呢?是該由誰來承擔這樣的責任呢?其實這樣的問題不難得出一個類比。譬如某人因為自己的問題犯了錯誤,最后由另外一個人來給他擦這個屁股。如果這樣的類比成立的話,很顯然,社會參與營救的費用就不應該算到公共資源上面,不應該由政府或者全社會來共同承擔。
應該由政府或者全社會共同承擔維護社會安全包括個體安全,正是政府主要職能之一。故而,應急救援服務是政府相關機構基于公民納稅的一項公共品提供,只能免費。
或許有人認為:并不是每個驢友都會不走尋常路而身陷險境,這些違規驢友無償使用大量公共應急救援資源,是搭了其他守法公民的便車;但是其實,在這個問題上,每個公民都是機會均等的。打個比方,要是誰家因自己不小心導致失火,有誰見過消防官兵要收費救火的?
無妨再換個思路:公共應急救援服務,能否作為準公共品,像路橋收取過路過橋費那樣,遵循“誰受益誰付費”原則,也收取政府性使用費呢?但細究下去,就會發現,此路不通。
一則,本著以人為本,生命至上的原則,遇險者應該第一時間得到果斷的救援,沒有“yesorno”
的選擇空間和時間,政府總不能因為成本的問題而撒手不管吧。就算是醫院也是要先進行搶救,等過了危險期在算相關的費用。
二則,事出突然,應急救援不計成本,甚至還有出動直升機搜救的,公共資源耗費巨大且不好預估,其中還充滿了種種變數,也難以做到像路橋等準公共品收取使用費那樣,預先設定政府指導價并明碼標價;哪怕就是設定政府指導價并明碼標價了,要是實際救援費用太過高昂,到頭來獲救者掏不出,也還是枉然。
三則,一些驢友不走尋常路,很多本就是違規的,存在重大的危險系數,即以此次事件來看,被困人員選擇的就是兩條非常規線路,需穿越大量無人區,這些線路從去年10月底到今年5月底禁止任何人穿越;若是付費搜救,豈不意味著有錢就可以違規,沒錢則只能悠著點?這樣的“贖買”只會消解相關法規的剛性,也于理不合。
那么,對于一些驢友不走尋常路,動輒因遇險導致大量公共應急救援資源為之靡費的行為,難道就只能聽之任之,全無制約辦法了嗎?
也并不是這樣的。驢友不走尋常路,既然多為違規行為,那就應該依法依規予以嚴罰重處。這才是解決問題的合適路徑。
按照國際慣例,所有搜救產生的費用將由被搜救者或者其家屬支付,或者由保險公司承擔,但國內目前在這方面的相關規定還不太健全。此前14名驢友在四川四姑娘山探險時既未進行備案,又違規走了一條被封閉的危險路段,結果引發搜救。這些驢友得救后被罰款1500元以及承擔3600元的部分搜救費用,但事實上,此次搜救總成本超過13萬元,其余部分最終還是由當地政府和景區方面埋單。
相關部門應該制定更為詳細的法規,明確戶外探險和搜救相關各方的責權利,并規范公共資源的使用。對違規行為要進行有力處罰,避免公共資源浪費。
救援費用“誰負責誰買單”
毋庸置疑,利用公共資源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進行救援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然而,作為納稅人的驢友,是否需要為救援費用買單呢?一方面,公共資源是用于拯救意外遇險的非責任人,驢友享有旅游的權利,政府應當保障旅游者的人身權利。驢友在法律所允許的旅游區域內實施探險活動,遇險原因系意外因素,如臺風、泥石流等自然災害以及其他不可預知的人為因素,政府應當對遇險者實施無償救助。
另一方面,權利的行使應當有邊界。明知會發生危險或具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主觀故意,驢友仍然按照既定時間前往既定地點實施探險活動,因其已經具有承擔危險的心理預期,其應當盡到規避風險的注意義務。
所以,那些自找風險者應當對其遇險救援費用予以分擔,而不能讓所有納稅人為自找風險者的遇險救援費用全部買單,分擔比例應當按照可預期程序予以酌定。如已經公開預告某地將在一定時間內發生自然災害,或明顯標識禁止擅自進入的區域,探險者堅信會規避風險而實施探險行為。
此外,對于救助資源屬于公共資源,還是非公共資源,非自找風險者無須承擔賠付責任,自找風險者所應買單的救助費用應當以全部救助費用總和乘以合理分擔比例計算。購買保險的自找風險者,由承保的保險公司按照合同約定進行理賠;未購買保險的自找風險者,自行承擔。
目前《陜西省旅游條例》第82條只是規定:“組織開展健身探險旅游活動未依法備案的,由縣級以上體育行政部門或者旅游行政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活動,對組織者處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嚴重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款……明知組織者未依法備案參與健身探險旅游活動,造成嚴重后果的,對參與者可以處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款。”罰則設置未免畸輕。今后有必要因應現實情況,在修法時適當提高罰金。一則,以對一些偏愛不走尋常路的驢友起到震懾作用;二則,所處高額罰金也能對搜救時巨大的公共資源靡費起到適當的彌補作用。此外,相關體育或旅游主管部門也得盡量強化前端的防控、監管,及早發現驢友不走尋常路的違規行為,并予及時糾正、懲處。
只有在前端“嚴防死守”,和在事后嚴罰重處,雙管齊下,才能盡量避免驢友不走尋常路遇險,把應急救援機構拖入泥淖之中,導致大量公共資源為之靡費的尷尬局面出現。
驢友不走尋常路,宜“嚴罰重處”,不宜“付費搜救”。“付費搜救”是個既缺乏法理基礎,又沒有現實可行性的辦法。
結束語: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黑名單”制度約束旅游專家、中國未來研究會旅游分會副會長劉思敏分析說,驢友戶外運動屢出問題的癥結有多方面:一是驢友安全意識淡薄、戶外知識缺失;二是組織機構準入門檻低,組織者專業技能有限,隨意組隊;三是行業內無相關法律法規進行規范約束。
劉思敏坦言,目前我國公共服務還沒有覆蓋到所有角落,對全部有特殊要求的游客提供福利性質的救援不現實。
一些業內人士建議,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但如果游客買了門票且走正常游覽線路時遇險,景區就必須負全責,這時救援就不宜收費。
多位資深驢友俱樂部領隊建議,可借鑒一些國家和地區對于戶外運動的管理法規,對商業性探險旅游的機構或俱樂部進行資質認定和管理,對于非營利性機構和個人從事相關組織活動,引入第三方機制進行引導。“如果措施得當,戶外運動事故率是完全可以下降的。”
專家認為,景區應嚴格劃定非探險區域,用增派人力、設置監控等手段防止驢友隨意進入。“針對屢教不改的驢友,景區和旅游管理部門可引入‘黑名單’制度,讓其為自己的過錯承擔應有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