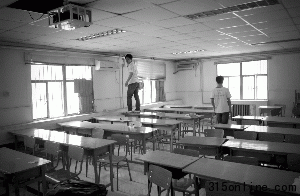剛剛開學,特崗教師張俊彩心里忐忑不安,她不確定,這個學期她的班上會不會有學生不再來上課。就在今年,學校5年級的一個班,就有10個學生輟學,無論老師們怎么勸說,家長和孩子都不愿回學校。
張俊彩所在的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丘北縣天鮮鄉發白村完小,有453名學生,其中73名學生來自周圍被撤并的5個校點。為了來發白村完小讀書,這些孩子最遠的要走6個小時,最近的也要走1個多小時。每當周末看著學生們用塑料袋提著書本走在回家的路上,崇山峻嶺中那小小的、孤獨的身影,總讓她有一種想哭的感覺。
日前,記者在云南部分地區農村中小學采訪時發現,由于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步伐太快、一些工作不配套,增加了農村家庭的負擔,造成了新的“上學難”,因上學路途遙遠,加之對孩子讀書后的前途不可預知,農村出現了新的輟學現象。農村孩子并沒有因集中辦學而變“上學”為“上好學”。
學校每天只能為住宿生提供兩頓飯
今年夏天,記者與云南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的團委副書記周鑫前往歸朝鎮龍門小學,給學校的孩子送雞蛋。這些雞蛋是云南青基會用募集的善款為龍門小學的山瑤孩子購買的。
山瑤是富寧縣瑤族的一個支系,又稱“過山瑤”。由于受惡劣自然條件限制,山瑤這一群體至今仍處于整體絕對貧困狀態。那里的孩子,一天也吃不上一個雞蛋。而云南農村中小學撤點并校,進一步加劇了山瑤孩子吃飯難、營養缺乏的問題。
龍門小學教導主任張玉龍告訴記者,學校239名學生來自周圍23個自然村,其中住校生160人。每個學生每月有75元的生活補助費。龍門是個缺水的村,學校每周要出去拉3次水,一車水15噸要150元;此外,食堂的柴火也要買,一車600元至700元,只能用1個月。如此一來,學校只能為學生提供午餐和晚餐。即使這樣,午餐也只能吃一個菜一個湯,晚餐則只有一個菜,一周吃兩三次肉。張玉龍給記者算了一筆賬,如果要給學生煮早餐,4個學生吃一把面,160個住校生就要40把面,以每把3元計算,每天僅早餐就要120元,這是學校無論如何都負擔不起的。
在文山州丘北縣舍得鄉礓嚓村完小,校長趙文一籌莫展已經很長時間了。周圍6個村的一師一校撤并后,礓嚓村完小147名學生中住校生增加到了113人,每人每學期交兩垛柴,在學校每天吃兩頓飯。然而,去年開始,由于沒有幼兒園,一些家長紛紛將五六歲的孩子送到學校,22個學前班的孩子不僅和一年級的學生擠在一間教室,還要分食113名學生的生活補助費。學校雇不起炊事員,老師們輪流做飯,紅豆、粉絲、洋芋、干菜,即使一頓只吃一個菜,老師們也只能選最便宜的。
“和爸爸媽媽在一起吃晚飯”是孩子們最大的愿望
除了100多名孩子每天的兩頓飯,令校長趙文擔憂的,還有他們每周上學、回家途中的安全。“很多學生家離學校太遠,一走就是四五個小時,存在很多安全隱患。”
由于路途遙遠,一些家長不得不每周接送孩子,甚至住在學校,負擔陡然增加。
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縣茈碧鎮碧云完小是一所集周邊8個自然村白族、彝族孩子就讀的中心完小。目前,全校23個住校學生住在兩間不大的土坯房里,最小的只有6歲。每周兩名學生家長到學校輪流照顧這些幼小的孩子。
富寧縣龍門小學因學生宿舍只夠50名女生住,其余90多名男生只能租住在周邊農戶的家中;礓嚓村完小100多個學生睡在100多平方米的宿舍里,全是地鋪。今年中心學校給完小送來13張1米寬的小床,校長決定,“一張床睡五六個學生,不能總讓他們睡地鋪,潮濕,會生病。”
“撤點并校加大了學校的管理難度。”趙文說,因住宿學生增加,教職員工承擔了大量本該由家長承擔的養育教育任務,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壓力。同時,年齡太小的孩子住校學習,生活也難以自理。
此外,由于長期寄宿,家長和孩子所付出的情感代價也不可低估。
張俊彩曾經讓學生寫下他們“最大的愿望”,結果許多孩子的回答完全一樣:“和爸爸媽媽在一起吃晚飯。”
“在所有的教育里,最可貴的應該是親情教育。”張俊彩說,但現實的情況卻讓這最可貴的教育缺失了。
這種現象已經引起了一些人士的關注。在今年政協云南省十屆四次會議上,云南省政協委員、云南省委副秘書長錢恒義就指出,云南中小學區域布局調整工作推進中,一些地區調整步伐太快,寄宿制學生劇增,寄宿生生活補助覆蓋面不足、資助標準低,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加重;學生的吃、住、衛生和安全保障考慮不周,存在疏漏;大量低年級寄宿生生活自理能力弱,家庭親情教育缺失,給學校管理帶來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