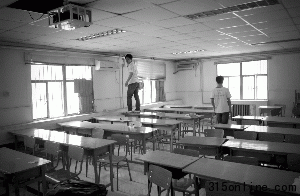在教育領域,“減負”不是一個新問題。長期以來,“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課業負擔”的呼聲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中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卻在“減負”聲中越減越重,成為嚴重影響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頑疾”。
對此,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認為,中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已成為家庭負擔、社會負擔,成為一種社會病態,“減負”刻不容緩。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認為,“減負”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學校、社會、家長要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要互相埋怨和指責。
八成中小學生學習超時、睡眠不足;片面的政績觀與用人制度是孩子課業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
孫云曉:首先要確認,當前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是很重的,有人認為并不重,是不對的。我們研究中心10年來對全國中小學生對比調查顯示,學生學習超時、睡眠不足情況越來越嚴重,1999年,近50%中小學生存在這一問題,但現在達到近80%,上升幅度驚人,城鄉都是如此。近年來我比較關注性別教育,發現男孩因為發育晚,理解力達不到,承受的學業壓力更大,但這并不意味著女孩就是應試教育的受益者,現在痛經成為中學校園常見病,這與女孩睡眠和休息不足、學習壓力大密不可分,最嚴重的是某省3例女生高考后出現閉經現象,經檢查為卵巢萎縮。這些只是冰山一角,中小學生的負擔已成為家庭負擔、社會負擔,成為一種社會病態。
張志勇: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周恩來就提出減輕學生知識學習的負擔,強調進行教材改革、教學改革,增加體育活動。我小時候上學,課業負擔遠沒有現在的孩子那么重。為什么我們改革了30年,教育發展了,條件改善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也大大增加了,孩子們的學業負擔卻越來越重?我個人認為,政績觀是主要原因,一些地市和縣市領導一說到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就看升學率,一說到評價和考核,還是看升學率,把教育事業等同于經濟和GDP,這種片面的政績觀綁架了教育,綁架了孩子。只要黨政領導將升學率看得高于一切,將教育與人的發展切割開來,無論是教育部門還是學校、校長,都無法安下心來按教育規律辦教育,而是一切按領導的意思辦,因為這樣風險最低,否則就不好對領導有交待。
孫云曉:還有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用人制度、用人導向有問題。現在用人單位以文憑取人,如果沒有一個大學本科畢業文憑,很難找到工作,如果不是名校畢業,就很難有好工作。這種高學歷就業、高學歷用人成為一種趨勢,其與中國人“爭做人上人、出人頭地、光耀門楣、望子成龍”的傳統觀念又呼應在一起,影響深遠。老百姓是很認實際的,我們又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很多父母尤其是獨生子女父母,對孩子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我們的一項調查顯示,83.6%的中學生父母希望孩子在班里考前15名,對小學生的要求就更高,這顯然是不可實現的目標。也是在這種導向下,升學率成為評價一個學校好壞的最重要標準,著名學校只要升學率下來,大家就都不認為它是一個好學校了。相關部門的政績觀也與此相伴而生。所以,課業負擔過重有著錯綜復雜的原因,是幾種力量匯合起來的結果。
學生負擔過重與違背教育規律相輔相成,拔苗助長,只會造成惡性循環;國家推行素質教育,本意是減輕學生負擔,但卻出現了將素質教育曲解為特長學習的現象
張志勇:學生負擔過重與違背教育規律相輔相成。當前教育中出現的拔苗助長現象,也在加重中小學生的負擔。一些幼兒園提前學習小學課程,在一些培訓機構里,小學低年級學高年級課程,高年級學初中課程的現象非常普遍。學校也在破壞學制,初中三年,只用兩年半完成所有課程,高中三年,只用兩年完成所有課程,這種違背課程方案,趕進度的做法,在加重學生負擔的同時,制造出大量差生,差生只能去補課,越補課越沒學習興趣,越沒學習興趣學習越差,造成惡性循環。
孫云曉:幼兒教育小學化傾向的后果是非常嚴重的。幼兒不適合進行系統學科教育,認字算數,游戲、運動、觀察和思考,更有利于幼兒身心發展。但是,一些父母為了讓孩子在選擇小學時在考試中占先,一定讓孩子接受學科知識的學習,一些幼兒園害怕失去生源,只好按父母們的意愿辦事。這真是太可怕了,這是人之初啊,對學習痛苦和扭曲的體驗,怎么會讓他在長大后對學習產生興趣?幼兒教育小學化,不僅對幼兒身心發展是個傷害,也是對民族創造力的傷害。
張志勇:這些年國家推行素質教育,本意是減輕學生負擔,但卻出現了將素質教育曲解為特長學習的現象。學生除了完成校內課程,還在校外參加各類特長培訓班,學習琴棋書畫等特長,考取各種證書,現在甚至奧數、英語也算是特長學習,一些孩子的夜晚、周末、寒暑假都要到培訓班學習,使他們的負擔愈發加重。教育是由學校、社會、家長共同來完成的,孩子學業負擔過重,家長也有一定責任。就拿特長學習而言,家長對特長是有誤解的,特長與天賦和興趣有關,如果僅僅將特長學習作為升學的砝碼,不僅不利于孩子的發展,反而會使孩子陷入更沉重的負擔之中。
減負不是中國教育改革的目標,重要的是改變學生學習的狀態、性質、內容、結構,狀態是要看學生學得主動不主動,性質是要看學生有沒有興趣去學;尊重學生的學習興趣,就要鼓勵他們適合做什么就做什么
張志勇:課業負擔,主要還是知識學習負擔,沒有人說學校的音體美課上多了。對于學校來說,如果國家規定的課程都開不齊,把學生在校時間都集中在知識學習上,顯然會讓學生感到無趣和有負擔。對于家長來說,在孩子走出學校的周末和寒暑假,應該進行一些非知識性學習,這類學習對孩子同樣非常重要,但是,家長仍把他們推向補習班,孩子只不過換了個時間、空間,所做的事仍和在學校做的沒區別,如果他們感興趣還好,如果不感興趣,也就變成了負擔。其實,負擔和有無興趣關聯密切,美國學生的負擔也很重,但是他們不覺得有負擔,就是因為他們以個人興趣為前提。
所以說,減負不是中國教育改革的目標,重要的是改變學生學習的狀態、性質、內容、結構,狀態和性質是一對關系,狀態是要看學生學得主動不主動,性質是要看學生有沒有興趣去學。結構和內容是一對關系,不能只將書本知識視為學習,必須加入非知識性學習。只學書本知識會使學生對學習失去興趣,學習效率降低。尊重學生的學習興趣,對于“減負”非常重要。
孫云曉:尊重學生的學習興趣,就要鼓勵他們適合做什么就做什么。在德國,就不存在學業過重的現象,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開始分流,一半以上進入職業教育,四分之一進入藝術類教育,準備考大學的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相對來說競爭和壓力都不大。德國職業教育的出路非常好,用人制度是適合什么就干什么。德國產品質量在世界屬于一流,與人才培養質量密不可分。中國目前也在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但是,很多人在內心并不認可職高或中專,甚至連大專也不認可。我們在職業高中調查,大部分學生表示他們知道職業教育很重要,職業教育也很適合自己,但是他們不喜歡職業教育,因為覺得丟人,抬不起頭來。人們心目中還是那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學業、就業、成功之路只有一座獨木橋——上大學,但是,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每個人都有出路的,一定是個立交橋,適合什么就走什么樣的路。因此,減負不能只在教育內部找原因、找方法,必須全社會共同想辦法。
地方政府要有正確的政績觀,學校要以學生為本,推進教學和課程改革;要大力推行有獨立資格的職業證書制度,在就業時具有獨立效力,而不是“高學歷+職業證書”
孫云曉:沉重負擔下形成的少數人成功,大多數人失敗的機制,一方面給個人制造了大量心理危機,誘發犯罪行為,另一方面也給社會心理造成不好影響。
張志勇:“減負”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地方政府、學校、社會、家長,各自做好各自的事情,而不要互相埋怨和指責。地方政府要有正確的政績觀。學校要以學生為本,推進教學和課程改革。社會要主動承擔起責任,更好地向學生服務,如加大小區公共圖書館和運動場館的建設,讓孩子放假了有地方可去,而不是直接被送進補習班。家長要承擔起教育責任,有時間盡可能帶孩子去博物館參觀,或是去旅游,加強孩子的非知識性學習。另外一方面,對于國家已經制定的法律、政策、規定,例如禁止在職教師有償家教、補課,禁止學校按考試成績排名次、小學入學、小升初禁止考試錄取等,如果能夠嚴格落實和執行,都會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中小學生課業負擔。
孫云曉:我給“減負”開個藥方:大力推行職業證書制度。這個職業證書是有獨立資格的,在就業時就具有獨立效力,而不是“高學歷+職業證書”。我強調這一點,是我女兒在日本時遇到的一件事給我的啟發,她的電腦壞了,電腦公司派來一名修理人員,很專業,把電腦修好了,這名修理人員是華人,不會講日語,也沒有什么學歷,但就憑著他的專業特長,他獲得了職業證書,從而實現就業。職業證書就要以職業為本,不要附加上學歷、英語考試等等,那不又成了學歷考試。成為全才的人究竟是少數,大部分人只能在某一兩個方面顯示出才能,職業證書只要能證明他的這一兩個才能就行。如果我們的用人制度以職業證書為準,而不是學歷,不僅學生的負擔減輕下來,用人單位也會少許多煩惱,畢竟目前用人單位也反映大學畢業生職業適應能力低的情況非常嚴重。(記者 王慶)